首次使用氢能作为火炬燃料、运营近千辆氢燃料电池车辆作为运输主力、配建30余座加氢站……氢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广泛应用,为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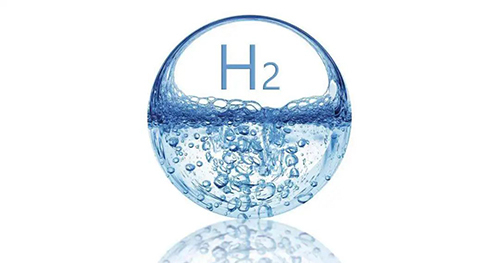
冬奥会闭幕不久后的3月,中国首个氢能产业中长期规划出台,提出了三个五年跨度的氢能发展计划。规划尤其强调工业副产氢短期内的积极作用,鼓励在焦化、氯碱、丙烷脱氢等行业聚集区优先使用工业副产氢,并提出了“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就近利用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的目标。
工业副产制氢是指将富含氢气的工业尾气(如氯碱尾气、焦炉煤气等)作为原料,通过变压吸附等技术将其中的氢气分离提纯的制氢方式。随着顶层设计出台,目前已有 30多个省市发布涉及氢能的规划和政策,其中,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都提出了要发挥本地的“工业副产氢资源优势”。
工业副产氢不仅成本低廉,而且能够促进周边氢能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但是专家认为,在“双碳”背景下,工业副产氢项目只能是短期的过渡方案,要避免对此领域的过度投资,尽快转向可再生能源制氢。
氢能不够“绿”
虽然氢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释放能量时只会产生水,没有碳排放,但是制氢的过程并不是百分百“零碳”。根据其生产来源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情况,氢气被分为通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灰氢、在灰氢的基础上使用碳捕集和封存(CCS)技术的蓝氢和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等手段所制的绿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生产国,年产量达3300万吨,占全球需求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能源结构看,全球氢气有60%来源于天然气、19%来源于煤炭,21%来自于工业副产气,电解水等低碳方式制氢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中国氢源结构目前仍以煤为主,来自煤制氢的氢气占比约62%、天然气制氢占19%,工业副产占18%,电解水制氢仅占1%。
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的氢源结构都不够“绿”,主要是受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根据能源转型委员会(ETC)的报告,全球生产灰氢的成本目前在0.7至2.2美元/公斤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天然气或煤炭价格。在此基础上安装CCS装置,变成蓝氢,成本将会必然超过灰氢,而最清洁环保的绿氢成本约为3-5美元/公斤。
从长远来看,想要发挥氢能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支撑作用,最清洁的绿氢无疑是最佳的,但是中短期内,工业副产氢被认为是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过渡方案。
作为工业大国,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简称“《白皮书》”)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工业副产氢的提纯成本在0.3-0.6元/公斤,考虑副产气体成本后的综合制氢成本约在10-16元/公斤。
工业副产氢仍属于灰氢,但相较于化石燃料制氢,它既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气污染,改善环境。《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焦炉煤气、氯碱化工、合成氨及合成甲醇、丙烷脱氢等工业每年能够提供百万吨级的氢气供应,在氢能产业发展初期提供了低成本、分布式氢源。
自国家规划出台以来,各省市不断加快推进氢能项目的实施。有媒体统计,2022年上半年共有18个制氢项目落地,其中副产氢项目9个,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9个,在数量上基本持平。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工业副产氢项目中,不难发现,利用工业副产气制氢只是其氢能发展的第一步而已。工厂生产出来的便宜氢气为其周边的区域以及所在的城市提供了建设氢能基础设施的契机。
用便宜的氢源打通产业链
氢能产业链分为制氢、储运、加氢站、氢燃料电池应用等多个环节。国际能源署(IEA)研究指出,想要发展氢能,需要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储运系统的支持,将供应端和需求端连接起来,建立一个高流动性的市场。中国目前已经开展的副产氢项目多采用“前站后厂,就近供给”的模式:在工厂的附近建设加氢站,为周边的氢燃料汽车、公交车以及工厂生产运输需要使用的重型卡车提供氢气。
以山东省为例,据初步测算,山东省年产氢气26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一,大部分为工业副产氢。2021年省内首个加氢母站在泰山钢铁集团建成投产,该加氢站能够辐射周边150公里范围的近百辆氢能汽车的需求,其氢气来源就是钢铁厂的工业副产焦炉煤气。随着加氢站的建成,山东重工集团的10辆49吨氢燃料电池牵引车也投入了运营。
内蒙古乌海市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由乌海化工的氯碱工厂产生的工业副产氢通过管道输送至工厂前方的加氢母站,再通过长管拖车运输至子站,为全市5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提供氢气。同时,乌海及周边地区总计8万辆矿山用车和柴油货车如果更新换代为氢燃料电池车,将提供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加氢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构建氢能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氢能产业链发展的薄弱环节。和氢气生产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成本是阻碍加氢站建设的重要因素。
《白皮书》数据显示,国内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500公斤的加氢站需要约1,200 万元,相当于传统加油站的3倍左右。除了建设成本外,加氢站的运行还面临着设备维护、运营、人工等费用,从而成了氢能产业的“卡脖子”环节。想要把产业链打通,加氢站和氢燃料电池车的供需匹配十分重要。若氢燃料电池车数量少,加氢站运营就没有经济性和规模效应。
IEA在上述报告中指出,使用副产氢有助于在工业中心获得低成本氢气并部署服务于工业的燃料电池卡车和公共汽车车队,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加氢站的利用率。这个模式解决了氢能部署主要面临的成本的问题。
工业副产氢项目不仅制氢成本低廉,而且由于接近应用端,储运成本也非常低。《白皮书》指出,在同一区域内的氢能价值链有机会发挥彼此之间的协同作用,例如在工业集群和运输走廊上的卡车车队可以依托更大规模优势降低总体成本。
山西的“柴改氢”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山西焦煤集团利用自有的煤炭焦化产能,提供低成本氢源,使用氢能重卡运煤,其产能全年可满足2200台重卡满负荷使用。参与该项目的国家电投国氢科技总经理张银广在采访中表示,煤炭基地外运量大且稳定,一个区域拥有成千甚至上万辆氢能重卡,为运营阶段规模化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只要氢气成本能够控制在25元/公斤以下,氢能重卡较柴油车就有足够竞争力。
挑战重重
工业副产氢在现阶段氢能供应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并不能够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其项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下游协同发展,不过氢能产业链仍存在“储运难”等诸多掣肘,过度发展工业副产氢有着锁定高碳基础设施的风险。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钢铁、化工等工业领域的产能必然下降,其副产气也会大幅减少,未来用工业副产气制氢必将遭遇产能瓶颈。河北省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河北焦炭企业数量将在“十四五”期间减少到40家左右,未来实际可提纯利用的工业副产氢资源总量也将从94万吨/年降低为约45万吨/年。
此外,目前现有的大部分加氢站采用外供氢源,需要依靠高压气态的运输方式,如果超过200公里,运输成本就会大幅增加。“就近消纳”是工业副产氢模式得以成功运行的关键,但并不是所有工业园区都能够像山西焦煤集团一样“自产自销”。储运环节成本高的问题受技术限制短期内仍难以解决。
独立能源分析师朱利安·阿尔米约(Julien Armijo) 认为,依托于煤化工业的工业副产氢在短期内可能是个机会,但是过分依赖工业副产氢是“危险”的,投资错误的基础设施会导致“碳锁定”效应。如果企业将用工业副产气制氢视为减碳的手段,反而延长了本该加速淘汰的高碳排放基础设施的寿命。
他指出,同样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经常声称蓝氢能够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因此应该作为大规模生产绿氢前的临时解决方案。然而智库E3G 的报告表明,这种方法反而会适得其反,蓝氢锁定了高碳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很有可能阻碍绿氢的发展。
阿尔米约也持相同的观点,“当企业倾注大量的资金去建设基础设施,他们通常期待其能够运营数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愿意对他们进行替换或淘汰”。E3G 建议,为了确保向绿氢转变,政府需要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和目标、问责制和透明度机制,以及支持逐步过渡的法规和标准,但是阿尔米约对此并不乐观,“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各国的行动都太慢了。”
转向绿氢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简称Merics)的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对氢能的政策支持仍以“产业发展为主,绿化为辅”。相较于旨在利用绿色氢能实现快速脱碳的欧洲战略,中国的氢能目标过于保守。
好消息是,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成本近年来持续下降,有望成为氢气来源的主流。ETC报告预计到2030年,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绿氢的成本将低于每公斤2美元。未来,绿氢在大部分地区将会比蓝氢、灰氢更便宜。
Merics的分析师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 表示,工业副产气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便宜的氢气来源,但仍属于灰氢,制氢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中国需要利用氢能来实现“双碳”目标,而只有绿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提醒中国不能依赖工业副产氢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如果中国认真对待其气候目标,就必须尽快转向绿色氢能。”






